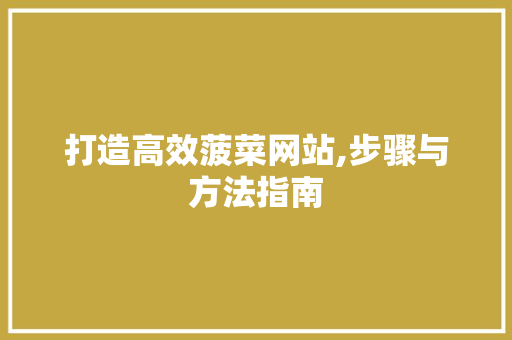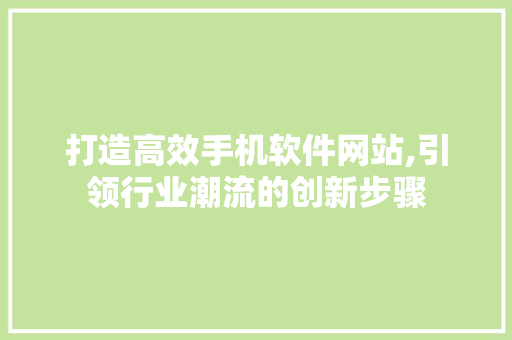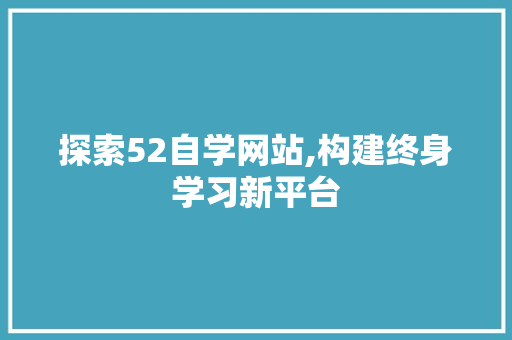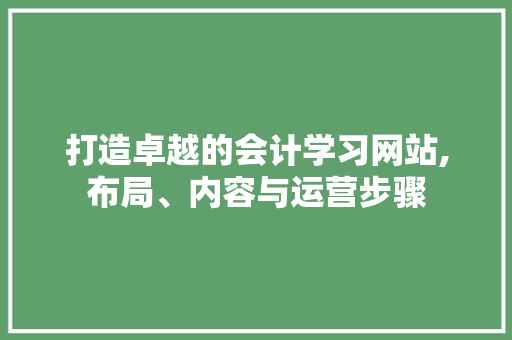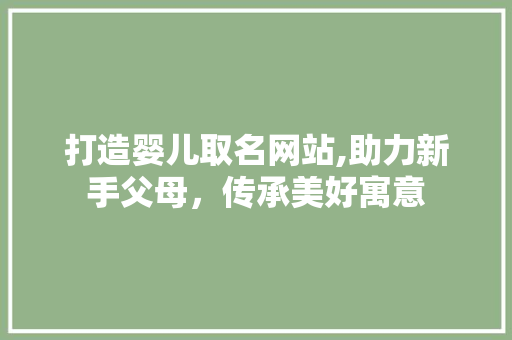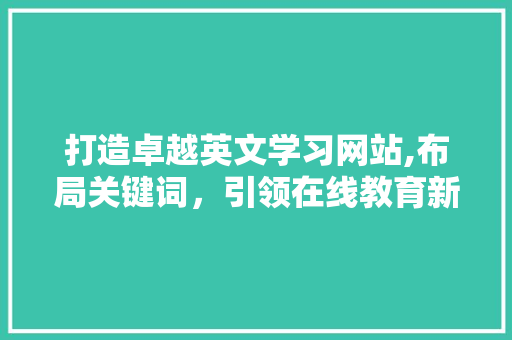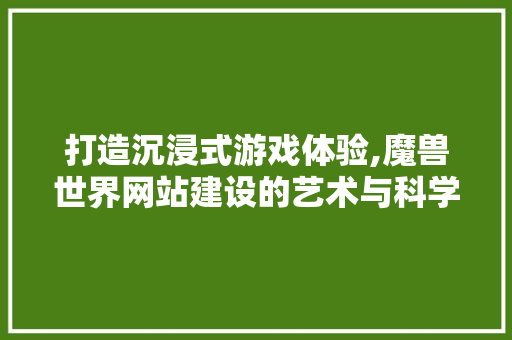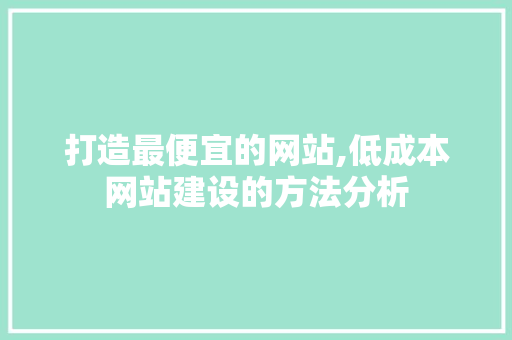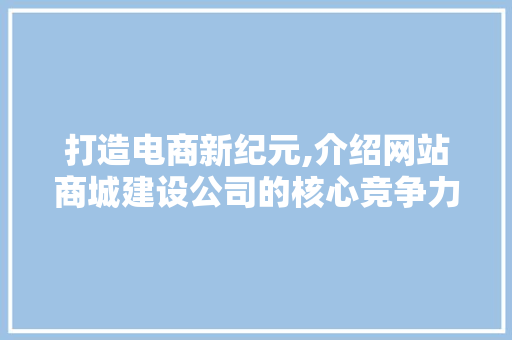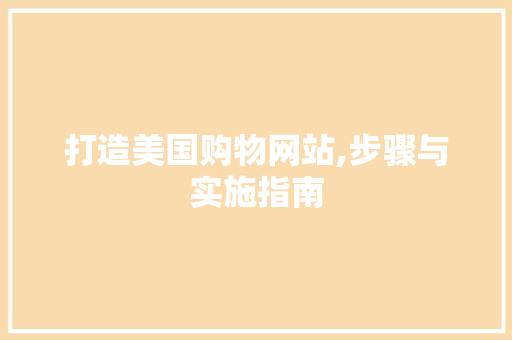最近一两年,“数字中台”这一观点溘然火了起来。不仅腾讯、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子纷纭着力培植数字中台,很多中小型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在内部引入数字中台。
与数字中台观点火爆相随的,是中台做事行业的迅速发展。据艾瑞咨询公布的《2019年中国数字中台行业研究报告》,2018年我国数字中台做事市场的规模仅为22.2亿元,但到2022年底,该市场规模有望达179.4亿元。未来,这个行业乃至可能发展为一个千亿元级别的市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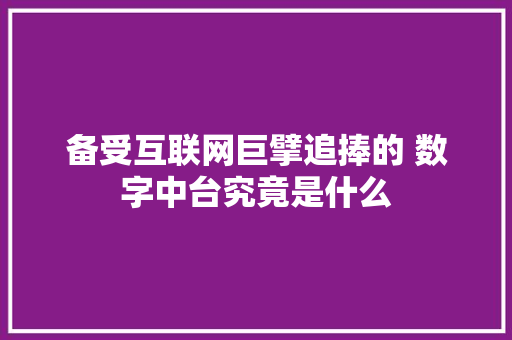
那么,如今火爆的数字中台到底是什么?它究竟有何用?企业又该如何培植自己的数字中台?
中台最早被运用于军事领域
从渊源上来看,中台实在是个外来观点。在英文中,它所对应的单词和“平台”是相同的,都是platform。由platform的含义,我们弗成贵知,它的浸染紧张是连接、沟通。不过,与一样平常的platform不同,中台是构建于企业内部的,位置处在前后台之间,故而得名。
最初,中台紧张被用在军事指挥上。在当代战役中,军队的单位变得越来越小,不同军种间的微不雅观合营变得越来越频繁,因此传统的指挥模式就不适宜这种作战办法了。为适应这种变革,美军率先发明了指挥中台,对前方作战单位进行统一折衷。在多场局部战役中,这种中台策略都发挥了主要浸染。后来,这种办法逐步被企业学习并采取。
就笔者所知,在海内企业中,阿里巴巴是最早采取数字中台的。2015年,该集团创始人马云参不雅观了著名游戏公司Supercell(超级细胞)。在参不雅观期间,他被这个仅有200人公司的高效所深深震荡。于是,他决定学习Supercell的做法,对阿里巴巴进行中台化改造,组建了“共享业务奇迹部”(Shared Services Platform),通过这一部门沟通前真个业务部门和后真个云平台。这次改革极大地提升了阿里巴巴内部各部门间的折衷能力,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内部各部门间在数据、产品等资源的共享。阿里巴巴的这种做法,很快被其他企业所效仿,由此催生了现在的“中台热”。
从构架上来看,数字中台包含人和物两方面。所谓人,是指居于企业内部,进行部门折衷的职员;所谓物,指的是对企业内部业务进行折衷的软硬件系统。对付一个完全的中台来说,这两者缺一不可。
中台蹿红与互联网商业模式有关
为什么数字中台会溘然在互联网企业中火爆起来?究其缘故原由,这和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有关。我们知道,平台模式是互联网企业最乐于采取的商业模式,而采取平台模式会带来几个主要的后果。
首先,同一个平台企业每每须要面临多个不同的市场,分处在不同市场的业务很可能差异巨大。其很可能导致,不同业务之间的事情职员缺少沟通,使企业内部互助很难进行,企业协力难以发挥出来。这就须要在企业内部由一个数字中台来实现部门间的沟通、冲破部门间的隔阂。
其次,采取平台模式的企业常会通过“平台包抄”计策,借助在原有市场上的上风进入新的市场。这就意味着企业随时可能“长”出新的业务线,使得原有的组织架构难以适应新变革。面对这种情形,企业当然可以通过调度组织架构来应对,但一样平常来说,这样做的本钱是巨大的。如果采取了中台化计策,那么就可以在坚持企业架构稳定的条件下,推进业务不断发展。
末了,对付多数平台企业来讲,数据都是最宝贵的资源。然而,在传统的企业组织架构之下,企业各部门、各市场之间的数据每每是不流利的,乃至数据的搜集和存储也各有各的规矩,“数据孤岛”征象十分明显。这样一来,企业就很难综合利用自己搜集到的数据信息来进行决策。而在建立数字中台后,企业就可通过中台实现不同部门之间数据的同质化处理,让数据在企业内部流动起来,这样就能大大提升企业利用数据的效率。
干系投资培植需理性剖析
虽然数字中台观点十分火爆,但作为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整合的一种办法,其本身具有很强的分外性,并非适宜所有企业,也不是所有企业都须要建中台。如果有些企业不顾自身实际情形,偏要凑热闹,为建数字中台而建数字中台,其结果很可能揠苗助长。
究竟什么样的企业须要建数字中台?
总体而言,它至少须要知足如下条件:首先,企业的业务范围该当比较广,不同业务间的独立性比较强、沟通难度较大。其次,企业对付迅速反应的诉求比较高。再次,数据在企业的决策中扮演的角色较重,不同部门间的数据隔离征象较为严重。笔者认为,只有知足了上述条件,投入资金去培植数字中台才比较划算。
那么,企业该当如何培植数字中台?
笔者认为,对付这个问题,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,须要根据详细情形而定。公司在实行中台计策时,必须要将顶层设计与底层推动有机结合起来。只管如此,在培植中台的过程中,如下两项原则是值得重视的。
首先,企业要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,统筹考虑外部需求环境、业务发展阶段、能力属性以及与组织形态的匹配性,以担保数字中台可以通过较强的实行力来冲破部门的藩篱,实行企业决策。
其次,企业应该充分调动部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,与数字中台形成良性合营,从而担保数字中台的折衷效果可以在不同部门表示出来。
(作者系《比较》杂志研究部主管)